记忆里的除夕碎片
编者按:这是一篇看似平淡叙事,却饱含历史厚重,感人至深的文字,令我们感叹过往岁月之沧桑,今日美好之不易。同时对毛小榕奶奶为代表,为这块土地抛洒汗水和青春的老一辈建设者,致以最朴实而尊崇的敬意。
今天是除夕,太阳终于出来了,核酸也暂告一段落了。我们连续做了四次核酸检测,小区宣布,至今小区里没有人出现阳性。虽然离我们最近的一幢楼某单元因为有一个密接人员被接走隔离,但我们的出行不受限制。因为我们仍旧在滨江区的“三区”之外(封控区、管制区、防范区),所以今天我就是做一顿除夕饭。而且全部菜品都是苏州口味的半成品,为我减轻了许多负担。
其实一说到除夕,我想到的竟然是小时候在军营里跟着警卫员到伙房磨米粉的场景:伙房里有一台大石磨,真正的靠两条胳膊拉着转圈的石磨。这是伙房做豆浆和豆腐的设备。平时它很忙,到了年边了,它竟空了下来。因为军营里需要糯米粉做年糕的人家,可能只有我们家了。
父母都是苏南人,说起来就是江南鱼米之乡出来的。邻居则清一色的山东人,这很符合当年华东野战军的结构。北方人吃饺子过年,南方人吃年糕和汤团过年。这是铁律。
我拎着一只铁皮桶跟着背着一袋米的警卫员,袋子里的米是糯米和粳米按比例混合的泡了一夜,这样可以磨出很细的米浆,蒸的年糕软糯合适,不会太粘牙。磨房里只挂着一只十五支光的灯,昏昏的灯下,石磨像一只艺术品闪着光,很是喜庆的样子。
我们把米放进桶里,警卫员推磨,我往磨眼里放米,石磨一圈圈转着发出嗡嗡的声音,磨杆吱吱响着很像小猫的叫声。我坐在那里添米,看着米浆从磨盘下渗出来聚在磨槽里,然后不慌不忙地流进捆在出浆口上的袋子里,好像日子一直是这么过着,吱吱嗡嗡一年年的没有尽头。这个回忆就是一部褪色的电影,很温暖。
米浆袋拎回家就放在洗衣板上,然后悬在洗衣盆上,袋子上压着一块洗干净的石头,清水就从布眼里渗出来,米浆就慢慢成了粉块。接下来就是妈妈的手艺了。出身江南人家的妈妈虽然是早早离家参加了新四军,但是江南人家的生活习俗一辈子也没有离开她。吃得讲究又接地气,妈妈曾经豪气万丈地说过一句话:“除了石头不能吃,什么都可以吃的。”
话虽夸张却也证明了江南人在食材上的物尽其用。完全可以和岭南人客家人分庭抗礼。
妈妈把摘来的竹叶洗净铺在蒸笼里,这几只蒸笼早几日就在水里浸泡好了,透着湿湿的暖意。米粉块调成细浆加上早就泡好的红枣和花生,一勺勺地舀进蒸笼里,差不多辅满三分之二的样子。炉子是离住房几米远的厨房的灶台,这是爸爸请管理科专门砌的南方人家常用的灶台,一边生火隔着一堵火墙便是灶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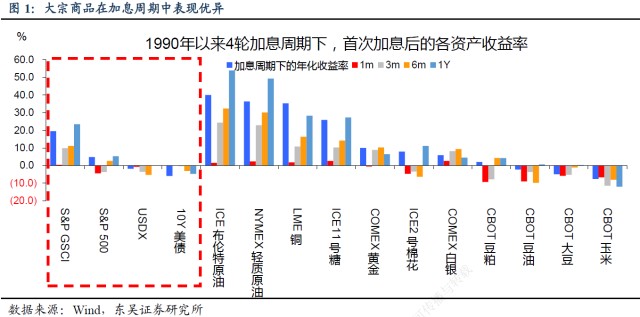
灶膛台旁堆着我和弟弟们早就劈好的松材。灶台上一只大铁锅腾着热气,蒸笼很快就压住了雾一样的热气。随着灶膛里柴火的添加,整间厨房开始像仙境一样,空气里全是红枣和花生的甜味。这是年的味道。照例妈妈是一夜不能睡的,因为灶火不能断,否则年糕就“死”了。
大年初一早上,我们的盘子里盛了煎好的年糕。每一块年糕都是切了片浸了蛋液再煎软的,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年糕,没有第二。
少年的除夕除了家,就是背着枪站岗的记忆。一九七零年的除夕。同志们在会餐过后散去,我们这些入伍一年的战士,开始军人生活的第一个除夕夜,背枪上岗。我服役的这家野战医院是离金门岛最近的军队医院。反敌特防水鬼在那个年代绝不是戏剧桥段。金门的探照灯很有规律地在晚上扫达天空,双方的炮击一过子夜就可以发射。所谓的“单号不打双号打”是以零时计算。曾经有一个新兵蛋子被天空扫过的探照灯吓哭了。我问他:“哭什么?你没见过灯吗?”他认真地说:“我们家在山里,没有灯。”
那个除夕夜,我背着五六式冲锋枪在军营里转着,听着对面广播站传送过来的音乐,居然是电影《刘三姐》的插曲《山歌好比春江水》。那时,这部电影已经被当成大毒草打翻在地了。
“唱山歌,这边唱来那边和,山歌好比春江水,过了一山又一山。”
就在除夕夜那天,我们的气球站又放了一批海飘。那些袖珍版的大白兔奶糖,茅台酒,都系在飘浮物上投进了海里,还有好看的样板戏明信片,乘风破浪顺海流飘向金门。
从小我就知道金门。因为我爸爸最亲密的战友徐博团长就在金门战役中牺牲了。当年在布置作战方案的会上,徐博坚持自己的意见:不能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攻打金门。会议结束后他对我爸说:“我回不来了,你让我老婆改嫁。”其实那时的“老婆”还是他的未婚妻。身为友邻团的团长,我爸知道徐博的意见是对的。这也是他晚年一直不能释怀的事情。
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。生活中被记住的细节就是一个人的人生观的印痕。
